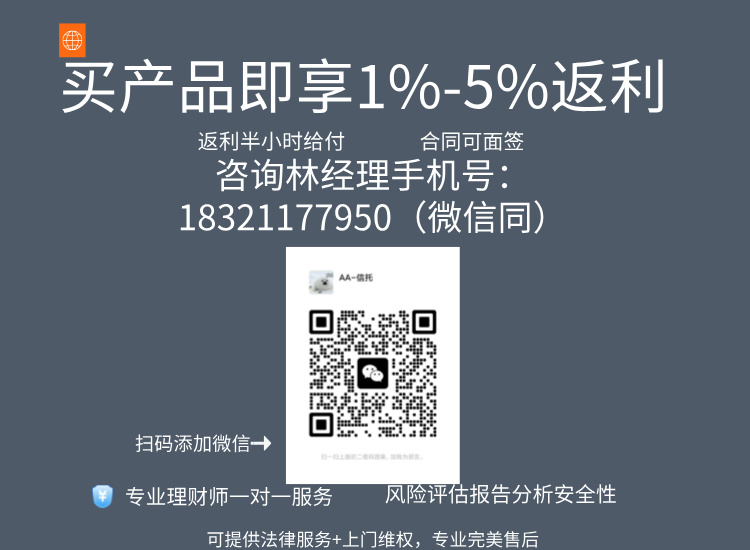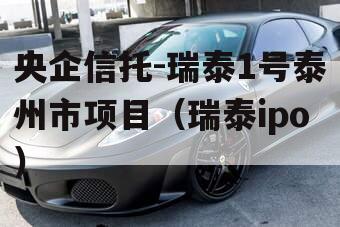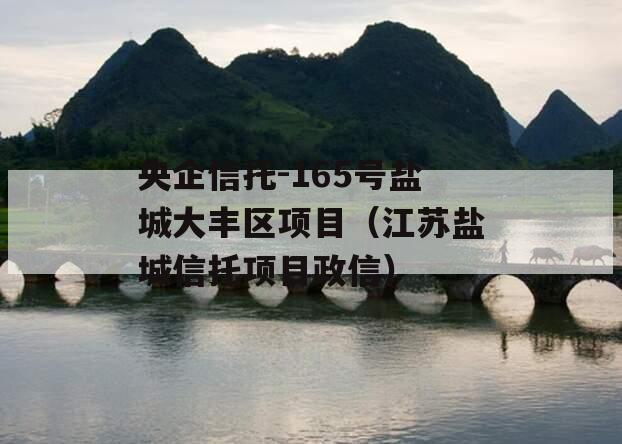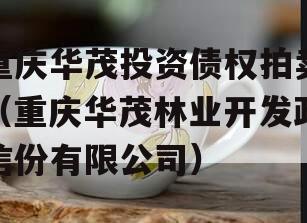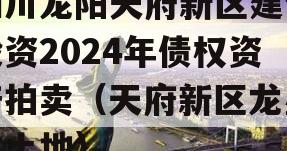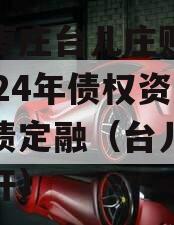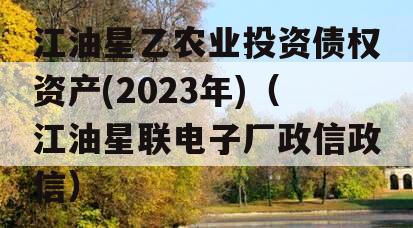摘要:
金石古欢— — 吴让之与吴云交游考述选自|《西泠艺丛》2022年第11期总第95期 |文/ 郑力胜、周逸阳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通过对吴让之与吴云存世的金石...
摘要:
金石古欢— — 吴让之与吴云交游考述选自|《西泠艺丛》2022年第11期总第95期 |文/ 郑力胜、周逸阳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通过对吴让之与吴云存世的金石...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金石古欢— — 吴让之与吴云交游考述
选自|《西泠艺丛》2022年第11期总第95期 |
文/ 郑力胜、周逸阳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吴让之与吴云存世的金石题跋、信札以及著述等文献的钩稽爬梳国企信托-一年期仪征非标,考述了两位学者艺术家之间的金石交游活动国企信托-一年期仪征非标,展现晚清时期金石学研究的各种细节情景,梳理清代金石学发展的轨迹与脉络。通过研究发现,吴让之曾长期为吴云作金石碑帖的鉴定、摹刻工作,并为之编纂了许多金石学著作,同时吴云的收藏也影响到了吴让之的书学实践。
【关键词】 吴让之 吴云 金石交游
一、二吴墨缘在长洲
吴让之(1799—1870),初名廷飏,字熙载,以字行,号让之。江苏仪征人。为晚清著名书法篆刻家,一生致力于史学、舆地学、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他的书画篆刻艺术,一直备受推崇,汪鋆在《扬州画苑录》中评吴让之篆书与篆刻当世无俪。[1]其篆书承邓石如一脉,出以飘逸用笔,创“吴带当风”的篆书风格。其篆刻一门亦为人推崇,所开创的劈削刀法对后世写意印风影响深远。吴昌硕尝语人曰:“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2]吴让之的画风意境淡远,风韵绝俗,以书入画,开“海派”之先河。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愉庭、退楼、抱罍子,别署二百兰亭斋、两罍轩,晚号退楼主人。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云少时家世坎坷,他勤于读书,博学多才, 却屡困场屋,直至32岁才考取秀才。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任常熟通判,后又权知宝山、金匮县。清咸丰三年(1853),其赴泰州任泰坝监掣官署。咸丰八年(1858),任镇江知府。咸丰十年(1860),任苏州知府。不久,以失地之责免职,因此丢官闲居,专力金石收藏与著述编纂。著有《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两罍轩彝器图释》《两罍轩印考漫存》等。
吴云幼承家学,喜习书艺。其书初从赵董入手,弱冠习《灵飞经》,行草学米芾。壮岁后,专宗《兰亭》,家藏二百多本兰亭拓本,朝夕摩挲,得其法乳。他在与李鸿裔信札中谈道:“余往来苏沪,遇有善本,固不惜典衣质卖,即近世复刻本亦搜罗不遗,积至二百余种。”[3]可见其对于《兰亭》的痴迷程度。晚年跟吴让之、何绍基交往甚密,故书风也介于二者之间,笔墨厚实而有鼎彝郁勃之气。吴让之、吴云作为晚清两位金石书画大家,交游深切,共同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
关于两人初次订交的时间,吴云在清光绪元年(1875)致李鸿裔的信中曾提及:
庚戌年,奉檄赴淮,僦寓扬州。晤同宗让之兄,一见如旧识,其年子贞兄由南入都,亦便道来访。三人同处,上下议论,讲求执使转用之方,博究篆分真行之秘,渐窥奥赜,始悔乖违。其时鞅掌奔驰,未能专学,悠悠忽忽,又逾十年。[4]
庚戌,即清道光三十年(1850),吴云在这一年任宝山县令,其奉上命僦居扬州。吴让之时入两淮盐运使童濂幕府,负责注《南北史》,后升任文汇阁分典秘书一职。同年,何绍基主持广东乡试结束,便道来访扬州。[5]三人共同论艺,“讲求执使转用之方,博究篆分真行之秘”。从这一年始,两人交往渐密。当时吴让之和何绍基均为52岁,吴云40岁,这三位好友,两位是学者、艺术家,一位是地方官员兼书画收藏家,因为共同的书画爱好而走到了一起。
从现有的史料文献来看,两人的交往主要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尤以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七年(1868)间尤多。吴云长期往来于江苏各地,而吴让之也经常寓居扬州、泰州等地,两人颇多交集,常有书信往来,关心彼此生活,寒暄问候。吴云就任镇江知府时,还经常邀请吴让之来自己官邸居住。咸丰九年(1859),吴让之在泰州收到吴云的邀约,临行前作《酬韬庵送行作》一首,题云:“余将之润州(镇江),赴平斋约。”[6]年过六旬的吴让之,外出访友的目的,除了艺术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协助好友研究金石,或鉴赏碑帖,或摹刻碑拓,或考订文字,或编纂著述,其乐融融。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吴让之的经济收入问题。
二、秦碑汉石共研求
吴让之与吴云在碑帖鉴藏研究方面的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吴让之为吴云刻了大量的印作。在吴云收藏过的金石书画作品上,也常常能见到这些印章的身影。
吴云在跋“归安吴云平斋考藏金石文字印”印蜕上言“攘之为余刻印数十百方”。可惜由于战乱等因素,吴让之为吴云所刻的印作存世已为数不多。主要以姓名、斋馆别号、收藏鉴赏印为主,分散于各大印谱。姓名印有“吴云私印”(图1);斋馆别号印分别是:“两罍轩”(图2)、“两罍轩”(图3)、“抱罍子”(图4)、“抱罍室”“退楼”两面印(图5)、“退楼”(图6)、“三退楼寓公”(图7)、“三退楼寓公”(图8)、“金石寿世之居”(图9)、“百镜室”(图10)、“簋罍斋主人”(图11);收藏鉴赏印分别是:“归安吴云平斋考藏金石文字印”(图12)、“平斋收藏金石文字印”(图13)、“簋罍斋考定金石文字印”(图14)、“平斋审定”(图15)、“平斋鉴赏”(图16)等。
◎ 图17 吴云致吴昌硕信札(一)
◎ 图18 吴云致吴昌硕信札(二)
吴让之为吴云所治这些印章,对后世印学影响意义深远。年轻的吴昌硕曾寓居吴云家中,见到了大量的吴让之印作,为其篆刻学习提供了许多借鉴范本。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多件吴云致吴昌硕信札,内容主要是吴云托吴昌硕治印,在回信时,常将印章钤盖于信上,附注评语,又出所藏吴让之印蜕附着边上,批注数语,勉励后进。如钤“退楼”朱文印(图17),旁注:“此印乃让之刻,章法殊妙。”又钤“金石寿世之居”白文印与“两罍轩”朱文印(图18),旁注:“此二印让之刻于田黄石,当日极为经意。”[7]此类批注不在少数。
这些信札有助于我们窥探吴昌硕印学成长的轨迹,也能看到吴云对这位同乡小辈的期望。吴让之与吴昌硕虽素未曾谋面(吴让之卒于1870年,此时吴昌硕27岁,仍居湖州安吉县),但却丝毫不妨碍“三吴”之间的这段传承交流,两人都曾先后寓居吴云家中,受到吴云的殷勤款待。在书法篆刻创作上,吴云深厚的金石学功底对两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吴让之和吴昌硕寓居吴云家中的那段时光均是两人艺术成长之路上重要的转折点,而吴云就是这段传承之路上的核心纽带。
第二,吴云常邀请吴让之在所藏碑帖上作题跋鉴定。
◎ 图19 吴让之跋《孔宙碑》
吴云曾致信好友许乃钊,称吴让之“于汉魏六朝碑版考鉴最精长”[8]。清咸丰六年(1856)八月,吴让之观吴云藏《孔宙碑》拓本,并作跋文(图19):
余旧藏有《泰山都尉孔君碑》,墨光黝然,锋端峻发,转折峭厉,一一具见。且未经割褾,颇自珍贵。今春见平斋先生此本,夺人心目,私心窃计“我有者亦不让是”,自标轴首曰“天下第一精拓”。携至罍敦斋与此本校,既多剥泐,又逊神采。主人笑曰:“君本亦不可多得,但须轴首所标‘一’字赠一画。”余惭而退。谚云:不可与海龙王比宝。信夫。[9]
吴让之以为自藏《孔宙碑》拓本足可媲美海内第一精拓,在与吴云藏本相校后黯然失色,因而有了“不可与海龙王比宝”的感叹。这也是两人的金石交流之中的一件为人所称道的趣事。
清同治三年(1864),吴云新得《汉东海庙碑残字》善本,珍如至宝,于册前题“海内无第二本”六字。吴让之获观后大为心喜,遂钤“熙载过眼”“熙载审定”二印,吴云又邀其写一观款,记其同赏金石之乐:“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夏四月,小寓集岩获观。仪征吴让之。时年六十有六。”[10]
◎ 图20 吴让之跋《洛神赋》
同年,吴让之又跋吴云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拓本(图20):
生平见《十三行》多矣,人咸推贾刻为上,实不敢知也。今见此本,殊有神采,殆前此所见者,伪劣下耳。然论《十三行》,当以《秘阁续帖》为至早,元宴斋为至精,鸿堂诸本以南廊库本为胜,再以此参之,庶不牖于形似。[11]
吴让之从版本角度着手,结合自身多年所见的各种版本,认为《秘阁续帖》为最早刻本,玄宴斋孙慎行刻本最为精湛,董其昌《戏鸿堂法帖》中所刻四本《洛神赋》以南廊库本为最胜。他还认为吴云藏本胜在“神采”,足以与其他善本相抗衡。
吴云曾购得张廷济旧藏秦度量衡,吴让之喜爱尤甚,近乎痴狂,借取数日,摹拓千百份,反复观摩。吴云在《两罍轩彝器图释》一书中就有回忆:
(秦度量拓本)乱后散失,归于余斋。曾携至邗上,家让之见之,焚香拱揖,正色谓余曰:“欲向君借取十日,手拓千百分,使行止、坐卧、触处,皆有此十二字,则吾老年篆法必有进境。”其倾倒如此,亦饶有米老癫疯风致也。[12]
吴让之的篆书在晚年已入臻妙之境,但其见《度量衡》,如若有新发现,新思路,孜孜不倦。这或许也可以理解成吴让之始终对自己的书法有着不断探索进取之心,至老不衰。
通过欣赏吴云所藏的诸多金石碑版拓本名品,使吴让之眼界大开,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说,吴让之帮助吴云编撰玺印类的书籍,从而让自己的印章增加了汉印之典雅意味,那么他通过对于秦汉拓本的欣赏和研究,亦使自己的篆隶更增加了几分古拙之意。
第三,吴云还延请吴让之摹刻所藏善本。
吴云喜欢摹刻旧碑,他曾购得《泰山刻石》旧拓,请吴让之钩摹,镌刻入石,存之焦山,于清咸丰八年(1858)刻成。吴云撰《焦山志》中著录此石,名为《重刻泰山二十九字残石》。
◎ 图21 吴让之摹刻《泰山刻石》
此摹刻本(图21)共四行,第一行“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九字,前二格与最后一格因风化严重,无法辨识;第二行“昧死言”三字;第三行“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十二字;第四行“矣臣昧死请”五字。
◎ 图22 吴让之跋《摹刻泰山刻石》(稿本)
第二行下方刻有吴让之跋文,有墨迹稿本传世(图22):
《泰山石刻》仅存二十九字,乾隆间毁于火,拓本日稀。仪征相国有覆本,藏之北湖祠塾。今归安吴公平斋云,来守镇江,亦得一古本,石无断文,属熙载刻之,嵌诸山寺。适《焦山志》成,补入金石类,以视来哲。咸丰八年六月,仪征吴熙载记。
◎ 图23 吴云跋《摹刻泰山刻石》
吴云跋文刻于第四行下方空白处,他在跋文中讲道(图23):
牛真谷运震《金石图》云:“泰山秦篆《二十九字》,在山顶碧霞元君宫之东庑,后有北平许氏跋,自‘御’字斜泐至‘石’字,中有断痕。”《潜研堂金石跋尾》言:“乾隆三年,碧霞宫火,秦刻遂亡。”此本旧为彭允初绍升所藏,有明嘉靖间人陈鲁南沂题记,碑中“石”字未断,无许氏跋。彭氏谓许名字不详,又无岁月,其书得古隶法而糢糊已甚,当是明中晚人,此拓本在嘉靖以前宜无许跋也。[13]
《金石图》为牛运震所著,成书于清乾隆元年(1736),而泰山刻石毁于乾隆五年(1740),牛运震在泰山刻石被毁前,已对刻石有过考察,而当时的泰山刻石中已有断痕之处。以此对比,吴云所藏本“石”字未断,亦无许氏跋文,也就证明了拓本必然早于许氏跋刻之前。且吴云藏本原为清初彭绍升所藏,附有跋文,认为许书“得古隶法而模糊正甚,当是明中晚人”。加上拓本中又有明嘉靖间人陈沂题记作为佐证,因此,两人订其为嘉靖前精拓。
三、周鼎齐罍有述作
传世的《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与《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是吴云最早的两本金石著述,在清代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本著述均是吴让之在咸丰年间寓居吴云家中协助其编纂而成的,据吴云回忆:“时正烽烟澒洞,侘傺无聊,相与考订金石。”吴云颇为爱惜,不轻易赠送他人,因此流传不多。
(一)《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图24)
◎ 图24 《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目录
《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吴云著,汪岚坡[14]摹,吴让之手书,柏刻匠镌,清咸丰六年(1856)刊行。封面为许梿[15]篆书题“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次为叶志诜[16]序,次目录,次正文。青铜器板块中,每件器物先由嘉兴汪岚坡缩摹,次附其器物形制、大小、重量等介绍,次铭文图释与释文,次考证跋文。
吴云编集《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吴让之是主要参与者、重要帮手。吴让之通文字之学,精研六书,对《说文解字》用功尤甚。汪鋆《师慎轩印存序》记载:“先生夙攻八法,旁证六经,而于许氏之学尤殚精焉。”[17]吴云在书中对每一器物的铭文做了翔实的考证,其中有多处参考吴让之的见解。如《齐侯罍》注:
家让之茂才熙载释作“其人民都邑”,“其”犹“之”也。
让之又云:陈氏释以齐侯罍为器断句,明此罍之为器也。意既成罍矣,何必自箸曰器也?他器亦鲜此文,意疑当训为作相为之“为”,明此罍为旅齐侯也。[18]
又如《庚罴卣》注:
韩履卿世丈释作“能”,谓即熊罴之“熊”省,家让之释作“龙”。
欧阳公《集古录》载“伯庶父敦为王姑周姜作”,与此正同,家让之云。[19]
再如《周伯舂盉》注:
右《伯舂盉铭》五字。“舂”,家让之疑是“杵臼”二字。[20]
综合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吴让之在当时确实为吴云的著述编纂下了许多功夫。
(二)《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图25)
◎ 图25 《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
《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吴云著,汪岚坡摹,吴让之手书,柏刻匠镌,清咸丰九年(1859)刊行。上海博物馆古籍部藏有两本,一为吴云自藏本,一为沈树镛藏本。首页为汪岚坡缩摹《虢季子白盘》全图,次《虢季子白盘》审定拓本,次陈介祺、吕佺孙、翁大年、张穆、瞿树宝释文,次吴云释文。[21]
从封面的题字可以看出,此书全名为《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吴云在跋文中称其为《虢盘考》。[22]此外,凌霞称其为《虢季子白盘释文》:“《虢季子白盘释文》一册。吴云录各家考释,而自加诠注。亦二百兰亭斋刻,吴让之手书。”[23]由于此书当年刊印数量极少,后又遭遇战乱,书版均毁于火,故吴云在清同治五年(1866)又刊印《虢季子白盘铭考》一书,内容与此书略有差异。
有了前二书的基础,吴云编纂金石著述的兴趣愈加浓厚。当其欲编纂《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时,首先便想到了吴让之。清同治元年(1862),他在致吴让之信札中说道:
弟现在编辑《吉金款识》,凡积古斋已载者不重录,其无关考证而迹涉赝鼎者,概行汰去。大约钟鼎簠簋敦彝尊甗之属,可得六百余种,类次十六卷。窃愿为积古之续,或即署《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此外,有《积古斋》所载而于原器铭文实有讹舛,如《邢叔钟》之漏刻数字者,拟另编一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订》,但论字文,不及考释,以免喜谤前辈之诮。所慨兵乱之后,故交零落,同好凋亡,兄又一江远隔,质疑问难颇少其人。现俟草稿粗定,明春安砚焦山,奉迓枉顾,就正有道,再行付梓。至释文仿《啸堂集古》例,疑者阙之,以省剞劂之费。[24]
吴云在信中感慨金石友朋多于战乱之后逝世,能质疑问难者日渐稀少,并就编纂《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构想以及编排体例、书名等问题向吴让之做了一番交流,约定次年共赴焦山编订。
结语
清同治七年(1868),吴云致函吴让之曰:“比来伤逝思旧,无可以言。与兄相晤两次,亦迥非昔时意兴。兄今年政七十耶,人生自堕地以至百年,莫不要从原路上去。弟薄有留赠,交存季谷处,并有说话属王吟轩转达。乔中丞与小云秋墅处均已面托,亦各有所赠。此数项统望留作正经用,不必归入开门七件事中。”[25]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两人交往最晚的文献记载。是年吴让之70岁,或许这不是两人最后一次的书信往来,但信中所述真实地反映了吴让之晚年的生活写照,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如此艺术巨擘每日还要为柴米油盐之事而犯愁。吴云始终在背后默默地关心和帮助这位多年的好友。
[1]汪鋆:《扬州画苑录》卷二,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2]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页。
[3]吴云著、白云娇辑释:《吴云函札辑释》,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27页。
[4]同上。
[5]据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记载,何绍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十日被任命为广东乡试副考官,同年八月主持乡试,结束后便返还入都,次年四月廿六日抵扬州城南泊。
[6]祝竹、朱天曙:《吴让之年表》,《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0年01期,第131页。
[7]浙江博物馆编:《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浙江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第40页。
[8]同[3],第53页。
[9]刘嘉成:《吴让之书法篆刻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第94页。
[10]《汉东海庙碑残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
[11]沈浩、康守永:《王献之楷书洛神赋十三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页。
[12]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413—414页。
[13]吴云:《重刻泰山二十九字残石》,《焦山志》卷七,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14]汪岚坡,嘉兴桐乡人。清代画家,曾寓居吴云家,助其编成《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
[15]许梿(1787—1862),清代学者、藏书家、书法家。初名映涟,字叔夏,号珊林、乐恬散人,室名红竹草堂、古韵阁、行吾素斋。浙江海宁人。
[16]叶志诜(1778—1863),清代学者、藏书家,字东卿,晚号遂翁、淡翁。湖北汉阳人,叶开泰第六代传人。
[17]汪鋆:《十二砚斋文录》,清光绪年间刻本。
[18][19][20]吴云:《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不分卷,清代刻本。
[21]柳向春:《上海博物馆馆藏珍本二种述要》,《上海文博论丛》2009年第4期,第24页。
[22]上海博物馆馆藏《二百兰亭斋金石记·虢季子白盘》,上有吴云于虢盘图后跋文:“……此《虢盘考》一册与《二百兰亭斋金石记》四册,皆其(吴让之)手书。”
[23]凌霞著:《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民国瑞安陈氏湫漻斋丛书。
[24]同[3],第85页。
[25]同[3],第86页。
《西泠艺丛》投稿邮箱 | xlyc2015@126.com
责任编辑 |王大啸、陈心怡